【编者按】
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是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其研究领域包括近代早期东南亚与东亚史、海外华人史、全球史。他与诸多上一代汉学家和东亚研究学者有过交往与连接。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个独特的爱好——驾驶帆船航行。本文是他驾帆航行随笔的第一篇,由孙蕴琦翻译。本文标题是一个双关语。在荷兰语中,“最好的舵手在岸上”的意思是“旁观者总认为自己比当事人做得更好”。
多年以前,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所住的房子位于哈赫斯豪(Haagseschouw)和德芬克车站(de Vink)之间的莱顿的莱茵(Leidse Rijn)河畔,房子的后院是一片水域,刚好够宽可以停放我们的荷兰小帆船(原文为“zalmschouw”,直译为“鲑鱼艇”,是一种大约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独具特色的荷兰捕鱼驳船,外观漂亮,适合内河捕鱼。此类帆船最初是木质的,后来也有钢铁渔船。这种驳船式的帆船具有特色的圆形船尾,让渔夫装载更多,也方便在船上站立和固定拖网。渔夫可以在河里一边划船一边捕鱼)。“瓦德里汉姆”21号(Woudrichem 21)。周末,在聒噪的海鸥陪伴下,我和妻子驾驶着小帆船通过莱顿驶向瓦尔蒙德村(Warmond),最后通过里德河(Leede)到达加赫湖(Kaag)。一个星期天我们再次出航,同船有两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这两位学者都在海洋史领域著作等身:关于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荷属东印度公司(VOC)在中国沿海的探险,以及西班牙大型帆船在墨西哥与马尼拉之间的航行。再远的海也不能阻挡他们的目光。
到了加赫湖,先把主帆升起,再升起前帆,同时把腰舵(zijzwaard,也叫披水板)沉入水中,“瓦德里汉姆”21号顺利地开了进去。当我们不打算向一个岛屿驶去时,同船的“船员”突然产生困惑!为什么要摆动风帆,转动腰舵?更不用说突然改变航向了。事实证明,这两位历史学家只研究关于坏血病、船上暴乱和船只失事这类事情,对如何驾驶一艘帆船一无所知。如今,你不需要穿着蓝色格子的水手服奔波于帆索之间就能成为书写水手生活的天才作家,但这样完全缺乏经验还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当我妻子拿这事开玩笑时,其中一位美国“岸上船长”诙谐地答道:没有飞行员驾驶执照,你照样可以写关于飞机的文章,不是吗?

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
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1887-1976)是一位非常了解海员生活的美国历史学家兼作家,我们在瓦尔多·皮尔斯(Waldo Pierce)绘于1940年的水彩画上可以看到他站立掌舵着纵帆船“七海”号(Seven Seas)。船上的另外三个航海伙伴分别是作家兼诗人林肯·罗斯·科恩科德(Lincoln Ross Colcord)、瓦尔多·皮尔斯本人,他也是个天才诗人,还有著名的民权律师扎卡利亚·查非(Zachariah Chaffee)。莫里森的右后方是叮当作响的小马南(Petit Manan)钟型浮标,小马南是缅因州海岸的一个半岛。这张附有各种幽默评论的速写画原是打算作为明信片寄给缺席的船员范·维克·布鲁克斯(Van Wijck Brooks)。

沃尔多·皮尔斯水彩画中莫里森和他的航海伙伴
莫里森据说是哈佛最后一位骑马去学校上课的教授,当他上课时,就用缰绳把他灰白色的马拴在院子里的一根柱子上。战争爆发前,莫里森仍穿着马裤出现在讲堂里,但后来他晋升为海军上将(退役),便穿着海军制服去上课。这给他的学生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学生惊叹道:“教授,您不必把我们当作下级海员那样说话。”
莫里森是一位追求优美文风的伟大学者,他认为许多年轻的同事在书写他们带有理论性质的学术散文时,应当受到掌管历史的缪斯女神克莱奥(Clio)的启发。如果每个学历史的学生在写论文前都先读一读他的小册子《作为文学艺术的历史:对年轻历史学者的请求》(History as a literary art, an appeal to Young historians),那么大学教育将获益良多。
莫里森两次将普利策奖收入囊中,被誉为20世纪最好的美国历史学家。信不信由你,毫无疑问,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作家,还创作了数量惊人的文学作品。出自他笔下的书就不少于50部,有些情况下,一部书还分为好几卷。你几乎可以想到,即使在马背上和海上,他也坚持写作。
艾略特·莫里森最初是因为他写的传记《哥伦布》而赢得声誉。在这本书中,他不仅仅在故纸和羊皮纸中爬梳保存下来的关于那位热那亚人航海大发现的所有信息,为了在加勒比地区的每个角落探索哥伦布的足迹,他还在1939年乘坐三桅帆船“卡皮塔娜”号(Capitana)前往里斯本,并搭乘42英尺(约12.8米)的二桅帆船“玛丽·奥迪斯”号(Mary Otis)返回美国。据传闻,1942年传记《哥伦布》一书的出版给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国家元首们还是喜欢阅读书籍而不是发推特——他立即派给莫里森一项特殊任务:书写官方的美国海军战争史。事实上,莫里森自告奋勇要求加入海军。他本人也认识罗斯福。在写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他提出不仅要服役,还要亲自参加海上的战争。“为了能以正确的方式去做,”他写道,“我必须在战火中去感受与海军鲜活的个人联系。”《二战时期美国海军战争史》(The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在15年的时间里(1947-1962)陆续出版了15卷。
除了严肃的史学著作外,莫里森偶尔也会写一些关于他和朋友的航海探险,最后在他年事已高之时写下他和第二任妻子普莉希拉(Priscilla)一起在缅因州沿海水域的旅行。几年前我就在缅因州波特兰市的一家二手小书店里找到《春潮》(Spring Tides)一书,是他献给普莉希拉的引人入胜的航海故事集。普莉希拉这位出生于费城的寡妇,之前从未踏上过甲板,最初她只有在多一位“能干的水手”同行的情况下才肯登上莫里森那艘36英尺(约11米)的高低桅帆船航行。“要是你掉下船我要怎么办呢?”她争论道。只要能不登船,她总能找到更好的理由。一天,莫里森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问题:必须把普莉希拉带到深海一次,之后她就会明白,仅仅他们小两口航行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儿。为了展示航海有多么容易,莫里森已经将他的“艾米丽·马歇尔”号(Emily Marshall)——看,36英尺(约11米)的高低桅帆船——装备妥当,展开船帆停靠在码头边上。准备好扬帆航行了!普莉希拉打扮得整整齐齐出现了,带着装满三明治的野餐小篮上船。在轻轻推开船首之后,莫里森接连犯了两个愚蠢的错误——愚蠢到我不想在这里赘述——他目瞪口呆地看到,他的小帆船带着甲板上看起来同样惊慌失措的普莉希拉正驶离岸边。幸运的是,普莉希拉知道除了快速行动别无选择。尽管她从未掌过船舵,她有模有样地学着启动了引擎,在原地转了几个迎风转向,并将主帆缭绳所在的吹管固定在船舵周围。她设法近距离地掠过了几艘游艇,在围观的每个人雷鸣般的掌声中,将高低桅帆船再次驶向码头,以便“岸上的舵手”莫里森还能跳上甲板。尽管这位勇敢的女水手从一开始就大喊大叫,但使这趟航行成为一次难忘之旅。

莫里森和他的妻子坐在他的高低桅帆船“艾米丽·马歇尔”号的驾驶盘处
《春潮》一书的标题来自书的第一章,里面讲述了春季潮汐的奇观,潮汐洗净了缅因州的所有小溪,并带来了成群的鲱鱼,当潮水退去,露出沙洲和岩石,正是采集各种贝类做一碗鲜美的蛤蜊海鲜杂烩浓汤的好时机。就像农民根据月球运行的位置进行耕种,水手和渔夫们相信,涨潮代表着力量,退潮代表着虚弱。莫里森听过一位医生这么形容一名年老的水手平静地吐出最后一口气:“他在退潮和落日的余晖中走了。”《一艘游艇的船舱》这章是关于1900年至1960年期间游艇内部装潢的怀旧之旅,从只有爬行高度的“狭窄空间”到拥有头顶空间的船舱,非常值得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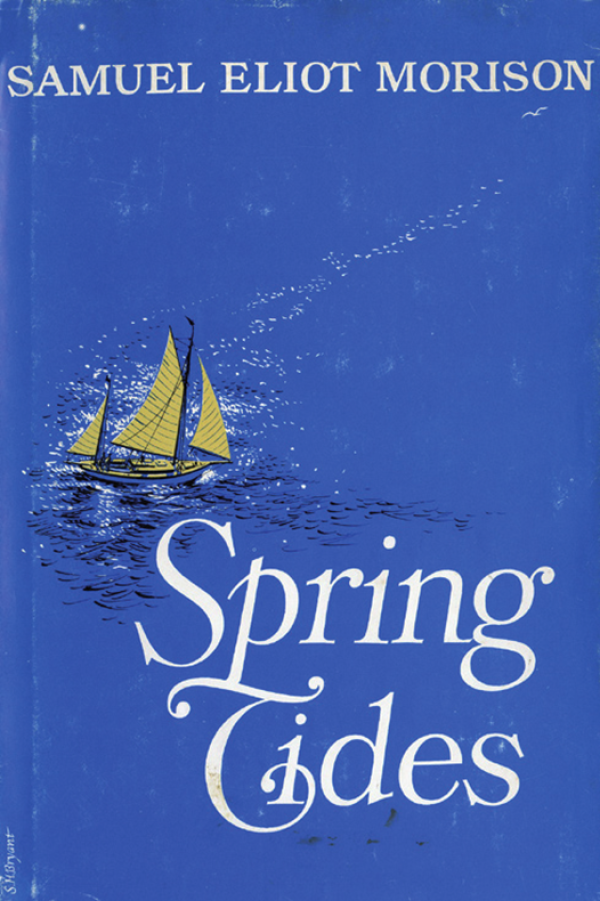
莫里森的短篇故事集《春潮》
二战前,莫里森乘坐一艘格兰特班克(Grandbank)港(纽芬兰岛南部港口,濒临福琼湾)制造的纵帆船(格兰特班特是位于纽芬兰东部的渔场,格兰特班特纵帆船是指一种用于捕鱼的双桅纵帆船)航行于希腊各岛屿之间,他发现阳光下的爱琴海呈现出葡萄酒红色,正如奥德修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的时代一样。那么,那些坐落在港口带露台的希腊小酒馆又是怎么样呢?当船员们一边兴高采烈地调整船尾靠岸,一边忙着松开船锚的缆索时,小酒馆的服务生已经端着一托盘的茴香酒倚立着向他们招手了。这也唤起我在上世纪60年代我与传奇的荷兰水手阿尔伯特·豪德里安(Albert Goudriaan)一起航行的往事。当时我获允乘坐他的“诺特的奥利维尔”号(Olivier van Noort)在希腊海域航行,那是一艘漂亮的淡蓝色海洋赛艇。此前一年,“奥利维尔”号在没有引擎的情况下,靠着大三角帆航行穿过科林斯海峡,并在被海岸警卫队抓住之前再次出航。
莫里森——这位历史学家再次出场——非常擅长引用希腊和罗马文学中的名句,以再现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经历的海上生活。他让我们看到,不仅《奥德赛》中描写的场景极度写实,甚至《使徒行传》第27章有关使徒保罗前往罗马的海上航程——如果你用海员术语去翻译——也有丰富的航海趣事可讲。我们的话题也就此进入到宗教领域,对航海的感情莫里森是作何感想呢?他承认:“我对大海的感情是这样的:写作关于大海的故事就像在做宗教忏悔那样让我难为情。”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